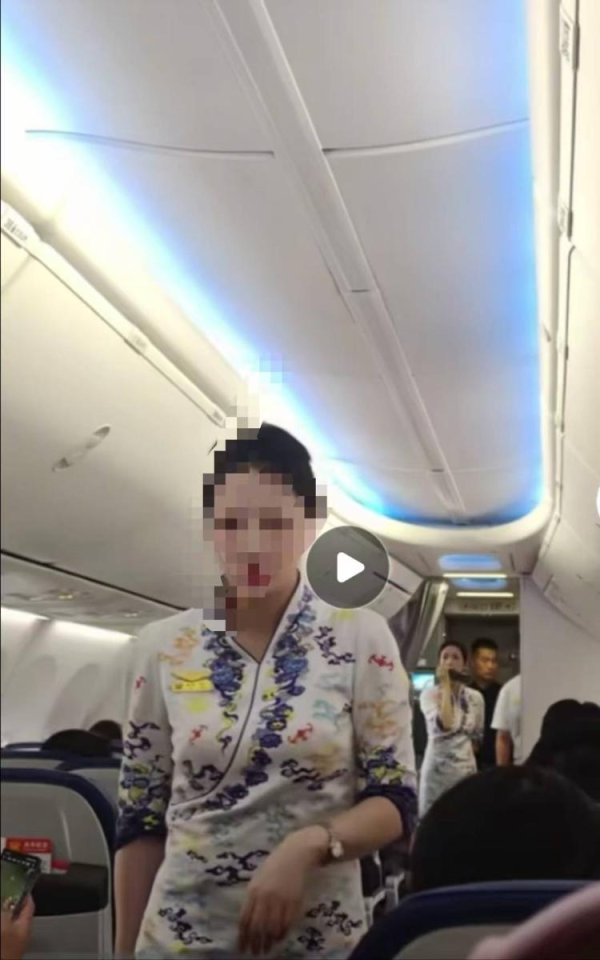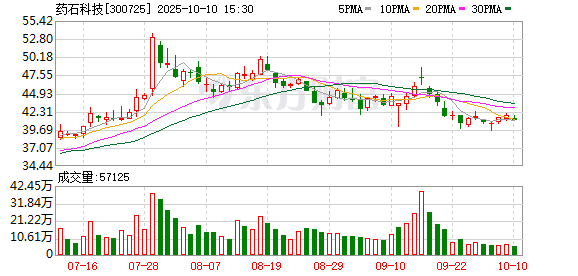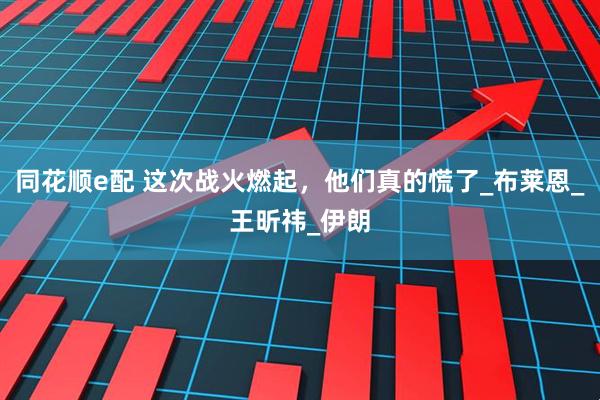
那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撕裂了德黑兰的夜空。36岁的沈阳商人布莱恩被突如其来的焦臭味惊醒,没来得及反应这是否为空袭同花顺e配,手机屏幕上的微信消息已经爆炸性地亮了起来。
在2023年6月13日凌晨3点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王昕祎也收到了来自国内导师和亲友的急切问候:“德黑兰遭遇轰炸了,你还好吗?”
那一刻,布莱恩和王昕祎都未曾预料到,这次袭击将会深刻地改变他们在德黑兰的生活。过去几年,伊朗虽有零星冲突,但从未像这次一样如此震撼。回想去年10月,王昕祎刚到德黑兰大学不久,也遭遇过一次导弹袭击,当时的爆炸声骤然而止,局势迅速平息,根本没引起太大的恐慌。
然而,这次情况完全不同。接下来48小时,局势迅速恶化,连王昕祎自己也承认:“从13号开始,爆炸声几乎整夜不息,白天也时不时传来。这种高强度、没有间歇的攻击,带来的心理压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
布莱恩的感受也几乎一致。他反复强调:“这次完全不同,以前的冲突是小打小闹,这回连伊朗人自己都感到恐慌了。”
展开剩余79%一切都变了
布莱恩第一次踏上伊朗土地是在十年前,当时作为一家中国汽车公司的外派员工。到了2022年,他看准了中伊贸易日益升温的商机,决定转行从事波斯地毯生意,并开设了旅行社,成为专注于中伊贸易的华商。
在德黑兰生活多年,布莱恩曾亲历过几次伊朗与以色列的小规模冲突。在他看来,过去这些冲突多为象征性质,类似“例行公事”,更多发生在边境地区。而德黑兰作为首都,总体来说是安全的。“只要不是全面战争,德黑兰基本不会受影响。”他曾这样安慰自己。
但是,2023年6月13日凌晨的袭击彻底打破了这种“安全感”。不到几个小时,布莱恩便接到了伊朗朋友的消息:“德黑兰东北部的居民区被精确打击,冲击波让我们家的玻璃全碎了,邻居家的孩子在爆炸中不幸丧命。”
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一袭击目标明确,袭击的居民楼住着多名军官。最终,袭击导致78人死亡同花顺e配,329人受伤。
然而,这场爆炸并没有在一夜之间结束。第二天的炮火持续不断,第三天依然如此,直到6月15日才稍微有所平息。王昕祎记得清楚,那天午后的阳光下,爆炸声依然不断响起。
随着焦虑感的加剧,生活在德黑兰的人们开始显现出紧张情绪。15日,王昕祎常去的小店和超市纷纷关门,他询问店主们打算去哪,得到的答复是:“去乡下避避风头,或者到其他城市待着。”网络的信号越来越不稳定,微信只能发送文字,图片再也发不出去。
布莱恩则发现出行变得异常困难。“我们叫不到车了,导航也不再精准。”他说,伊朗当局为防止导弹精准打击,干扰了GPS信号,导致地图出现偏差。14日时他还能叫到车,但到了15日,几乎所有出行方式都停滞不前。
“14号那天,我还去商场吃了顿饭,当时觉得事情似乎没有那么严重。但第二天再去,商场已经关门了。”布莱恩说,“许多德黑兰人已经开始撤离了。只要有能力的人,哪怕是到乡下或者去其他城市待一阵,也都在尽早离开。”
以往,伊朗人对类似的袭击早已习以为常,认为这些仅仅是政治作秀,但这次,连他们自己都开始感到恐慌。
紧急撤离
原计划16日离开德黑兰的布莱恩,在形势急剧恶化后决定提前撤离。15日下午,德黑兰再次传来爆炸声,他紧急调整计划,准备次日离开。
为了确保顺利撤离,布莱恩迅速组织了一辆大巴,并联络了17名在德黑兰的中国同胞。利用自己经营旅行社的资源,他临时安排了一条撤离路线,急忙集结队伍,准备连夜出发。
然而,王昕祎的撤离之路并不顺利。当时,他所在的撤离队伍遭遇了大规模的交通堵塞。原本十小时的车程,因道路拥堵和油料紧张等问题,竟然花费了二十多个小时。
布莱恩则在路上遇到了一系列挑战。他发现伊朗政府对每辆车的油量进行了限制,导致加油站排起了长队,路边停满了无法启动的私家车。幸运的是,由于他们的大巴车使用柴油,而非汽油,才得以继续前行。
布莱恩带领的队伍最终选择前往亚美尼亚边境,绕过了阿塞拜疆口岸。凌晨时分,他们终于抵达边境,开始了长达十小时的山路之旅。
与此同时,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也在积极组织撤侨。另一批由华人华侨联合会协调的撤离队伍也在同一时间从阿塞拜疆口岸出境,而王昕祎正是其中的一员。
“接到撤离通知时,我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王昕祎回忆,“带的行李很简单,除了博士论文和几本书,我只能带走一些换洗衣物和几件伊朗的纪念品。”
当他告别房东时,房东仍然坚持不接受他剩下的钱。临别时,房东用不太标准的中文语法说:“你最好的我中国朋友。”说完这些话,转身消失在德黑兰空寂的街头。
离开与归属
布莱恩的离开让他感到十分复杂。“当时仓库里堆满了价值上百万的波斯地毯,连那批已经打包好的货物都没来得及发。”他说,随着战事升级,物流中断,许多合作伙伴也选择暂时逃离。
与布莱恩不同,王昕祎来伊朗更多是为了学术研究。他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生,研究方向是伊朗现代戏剧。过去的八个月,他深度参与了德黑兰的戏剧演出,访谈学者,收集第一手资料。
“伊朗的戏剧发展比我们想象的更现代、更开放。”他说,“尽管面临制裁,伊朗学者依然坚持学术研究,参与国际会议、发表高水平论文。”
在撤离的过程中,布莱恩和王昕祎都深刻体会到战争带给普通百姓的痛苦。“我在伊朗有很多朋友,他们过得很不容易。”布莱恩感慨道,“我希望他们不再为生计发愁,也希望这个国家尽快恢复和平。”
尽管两国达成了停火协议,布莱恩和王昕祎都深知,停火只是暂时的,随时可能会有新的冲突爆发。
布莱恩依然记得,撤离那天的大巴在漫长的堵车中停滞不前,车上的伊朗司机突然拿出梳子,对着车窗反光镜认真梳理起了胡须,仿佛在寻找一丝片刻的宁静。
这一次的离别,可能比以往更加永久同花顺e配,或许,他们再也无法回到曾经熟悉的德黑兰了。
发布于:天津市恒汇证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